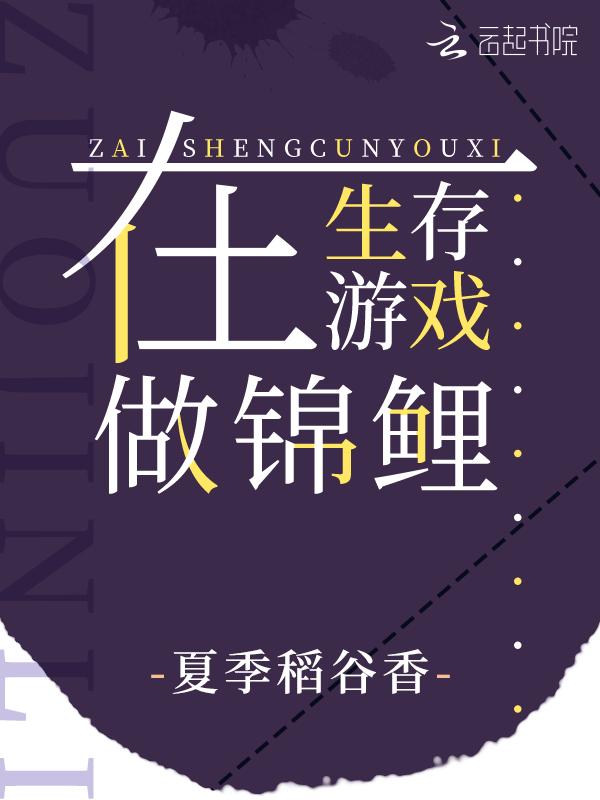《四合院:从截胡秦淮茹开始》673 张家产业迅速膨胀外国品牌上门求代工催何雨水马华成婚
一眼话筒,显然是对被坏了好事感到不满。 兴致遭到破坏,李怀德眉头紧皱的接过话筒,冷声道: “喂!是谁?”... 夜深了,四合院的灯火渐次熄灭,唯有秦淮茹窗前那盏煤油灯还亮着。她伏案疾书,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像春蚕啃食桑叶,又似细雨敲打瓦檐。墙上的老挂钟滴答走动,已是凌晨两点。她揉了揉酸胀的眼睛,将写好的《平民女子法律学堂招生启事》轻轻吹干墨迹,叠好放进信封。 明日便是周六,第一堂课开讲的日子。 清晨五点,天刚蒙蒙亮,刘海柱就拎着铁皮桶去胡同口接自来水。水龙头哗哗作响,惊醒了隔壁贾家的小孙子。孩子探出脑袋一看,只见刘海柱正蹲在地上刷洗三张长条板凳,擦得锃亮。“刘叔,您这是干啥呢?”小孩好奇地问。 “今天咱院里要...
《四合院:从截胡秦淮茹开始》最新章节
- 673 张家产业迅速膨胀外国品牌上门求代工催何雨水马华成婚
- 672 刘海中要当大老板许刘掏空家底孤独一掷不知黄雀在后
- 671 办公室知男女真情意李怀德设局试探差点失身的许大茂要自立门户
- 670 张元林展现社会责任感马华示好何雨水刘岚又送情报又当大客户
- 669 为报恩娄家无条件投资娄晓娥贼心不死张元林公开宣布与娄家合作
- 668 娄晓娥带儿子认亲张元林合理安排获二女认可阎埠贵造谣再当小丑
- 667 万元项链价值几十许大茂怒找李怀德讨说法娄晓娥带孩子归来
- 666 万元项链价值几十许大茂怒找李怀德讨说法娄晓娥带孩子归来
- 665当街笑看狗咬狗低价盘下阎解成饭馆张元林用医院照片换来最后一面
- 664 张家饭馆开业爆满阎解成被掀桌投诉破产秦京茹病逝送出房契
- 663 老人们声讨阎家入伙张元林院内新增锻炼器材赢好评京茹父母拒见
- 662 赚钱后阎解成过河拆桥踢傻柱冷嘲热讽笑父母张元林为承诺开饭馆
《四合院:从截胡秦淮茹开始》章节列表
- 第1章 是该娶个媳妇了
- 第2章 这年头单身有罪啊连贾家也惦记上了自家房子
- 第3章 抛锚的汽车和19岁的秦淮茹
- 第4章 主动显山露水让你们开开眼
- 第5章 自我介绍展示人脉免费吃喝拿秦家的震惊
- 第6章 开始收网带着未来媳妇和岳父岳母体验白嫖的快乐
- 第7章 真不好意思我也没想到这波装大了着实是吓着了你们
- 第8章 高端玩家张元林从贾东旭开始降维打击
- 第9章 贾东旭在大院里干吹牛皮张元林在火锅店大报菜名
- 第10章 不知不觉间秦淮茹芳心暗许秦父秦母只想认张元林做女婿
- 第11章 张元林计划的最后一步虾仁猪心
- 第12章 淮如登场男默女妒为看热闹张元林备好花生瓜子
- 第13章 有张元林作比较贾家家丑外扬从里到外都差劲的不行
- 第14章 被拒绝的贾东旭原地哭闹贾张氏大骂秦家乡巴佬
- 第15章 见贾家和秦淮茹再无可能许大茂和傻柱也想截胡
- 第16章 张元林霸气镇场淮如可是我妹妹两个大逼兜教贾家做人
- 第17章 几句话吓的贾家母子腿发软易中海脸色铁青聋老太太被迫登场
- 第18章 谁的面子也没我心里舒服重要一年工资加全院检讨道歉
- 第19章 秦淮茹表白张元林大院轰动贾东旭再当小丑泪奔离场
- 第20章 预料之中的美好结合计划之外的免费媳妇
- 第21章 不花钱还不办酒怎么行就拿贾家的赔偿来办吧
- 第22章 一手漂亮的道德绑架气晕贾张氏让易中海麻到怀疑人生
- 第23章 钱是落袋为安媳妇要领证才算
- 第24章 秦淮茹一进家门就开始忙活嘿就是要娶这样的
- 第25章 给准媳妇先上一课来自秦父秦母的叮嘱
- 第26章 送准岳父旧手表张元林的人生理念
- 第27章 出门领证大院各家反应易中海数钱数到头晕手抖
- 第28章 一大妈的酸楚阎老西的算计
- 第29章 托付愿了告别好女婿是我们高攀了
- 第30章 教导小媳妇吃喝不能省张元林展示父母资产
- 第31章 三房四铺秦淮茹的惊讶与担忧
- 第32章 带秦淮茹定制新衣张元林意识到结婚是个清库存的好机会
- 第33章 靠人情白嫖两套新衣老板娘拉着秦淮茹试新妆
- 第34章 轻妆淡抹惊艳时代老板娘请吃饭被婉拒别闹春宵一刻值千金啊
- 第35章 带个天仙媳妇回家贾东旭偶遇泪洒胡同掩面而逃大院全员接连看呆
- 第36章 秦淮茹结交的第一位大院邻居两人俩菜小两口第一顿家常便饭
- 第38章 贾东旭丢了易中海发动全院找人
- 第39章 一大爷好人不是你这么当的
- 第40章 三轮车夫老徐眼中的张大财神
- 第41章 为了面子连句谢谢也没有活该你被贾家坑
- 第42章 这才一天结婚的没结婚的都出名了
- 第43章 老是白拿多不好意思我脸皮很薄的
- 第44章 带媳妇儿瞧瞧一大爷的办事手段
- 第45章 正所谓一物降一物我张元林一人降全院
- 第46章 老徐带回贾东旭易中海不想掏钱道德绑架全院
- 第47章 易中海和贾张氏的表现不尽人意张元林要做拨动众人命运的那位
- 第48章 三位大爷内讧聋老太太搅局
- 第49章 好人还得张元林来当与老徐互飙演技吓坏众人
- 第50章 把钱付了吧再继续还下去就不礼貌了
- 第51章 老徐懂事的孝敬张元林的刻意而为之
- 第52章 易中海的难堪和委屈聋老太太的表态
- 第53章 我就想加个汤不断退而求其次的张元林
- 第54章 父母的对比和孩子的不服傻柱一句话点醒何大清
- 第55章 张元林成了饭桌上无法避开的话题各家的谈话与想法
- 第56章 易中海的应对借花献佛功在自己
- 第57章 酒席倒计时主要还有置办家具和找大厨这两件事
- 第58章 何大清强买强卖贾东旭献丑
- 第59章 徒弟丢脸自己送钱好人易中海失眠难受一整夜八千求首订
- 第60章 懂事的小媳妇就是让人喜欢张元林准备更换全屋旧家具求全订
- 第61章 傻柱求张元林接连碰壁何大清和易中海同时盯上了婚宴求全订
- 刘海中和阎埠贵真香警告全院跟着哄抢张元林家的旧货求全订
- 第63章 张元林独自搞定所有老板娘赞叹贾东旭又脑抽求全订
- 第64章 好事将近试新衣塞红包画妆容接亲家求全订
- 第65章 新人新衣新妆容喜糖喜烟喜事到张元林全院撒币热闹成婚
- 第66章 贾东旭抹黑张元林狂扁小朋友大小战神正义出击求全订
- 第67章 礼成开席哪有什么千杯不醉不过是外挂到位罢了求全订
- 第68章 刘海中被呛贾东旭捡窝头听秦家讨论秦京茹全院吃飘了
- 第69章 傻柱被套路卧龙凤雏搞事张元林送秦家人上车倒拿钱求全订
- 第70章 何家父子一唱一和易中海老太太帮腔张元林笑看何大清作死
- 第71章 众人白嫖失败刘海中主桌无望许家丢人何大清承包张家晚饭
- 第72章 易中海被呛心中不爽劝说聋老太太联手算计何大清只为掌控傻柱
- 第73章 被土特产和活禽堆满的房间这怕是举族之力陪嫁啊求全订
- 第74章 干点活还能享受贴身服务贾张氏找易中海算账带了盆泔水回家
- 第75章 贾东旭窜稀挨饿一整夜贾张氏藏粮张元林神乎其技惊呆全院
- 第76章 活禽饲养特产晾晒全院掏钱预订养殖屋一大妈找秦淮茹唠嗑
- 第77章 两个女人互比男人张元林为爆款定价话题席卷全厂和街道处
- 第78章 街道主任上门委以重任张元林想全拿下贾东旭也凑热闹易中海麻了
- 第79章 贾东旭认怂被夸谦逊师徒俩当场自闭贾张氏撒泼反咬引一大妈发火
- 第80章 易中海备考七级工阎埠贵眼红张元林赚钱秦淮茹展现顶级天赋
- 第81章 小媳妇真不错再给老徐介绍生意易中海为保面子帮徒弟作弊考一级工
- 第82章 许刘两家的野心易中海忽悠贾家门卫乱说话的影响还是来了
- 第83章 画室完美操作被邀娄家做客百花簇拥被许父破坏对症下药现场开整
- 第84章 街道办张贴名单是谁给贾东旭的勇气许父被揪耳朵傻柱喊看瓜
- 第85章 大院跟着出了名许家父子坦白局易中海再忽悠傻柱求全订
- 第86章 修补如新画功绝伦娄父娄母后悔张元林乐了求全订
- 第87章 娄父欲加注奖励维修部的震惊与欢呼勤学苦练贾东旭求全订
- 第88章 吃瓜群众的议论大爷们的博弈刘易接连考级成功 求全订
- 第89章 阎埠贵欲模仿张元林铩羽而归秦淮茹高光时刻震慑全场求全订
- 第90章 大院各家的混乱一片张元林的牌面打工人的梦求全订
- 第91章 众领导套话失败白送钱礼三位大爷搞事引起张元林警惕求全订
- 第92章 一大妈通风报信院内开启大相亲时代求全订
- 第93章 聋老太耳朵真出了问题易中海精神崩溃建议加大药量求全订
- 第94章 整个四九城都是张元林的猎场考场负责人发现易中海计划的又一漏洞
- 第95章 各方为抢夺张元林持续下注贾东旭报喜易中海脸都绿了求全订
- 第96章 师慈徒孝和母慈子孝求全订
- 第97章 贾东旭作死挑战张元林贾张氏为相亲定下四条规矩求全订
- 第98章 许大茂和傻柱试探工作继承问题三位大爷家里各有难念的经求全订
- 第99章 让易中海忌惮的陈年往事贾东旭见面就开始骚操作求全订
- 第100章 张元林展开精准分析秦淮茹崇拜贾家试图白嫖被臭骂求全订
- 第101章 媒婆怒喷易中海广为宣传贾张氏强行赖上易中海气哭一大妈
热门小说标签
悔婚怎么处理违法吗?天下无敌!李先正版笔趣阁李先天下无敌!最新更新章节免费阅读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天下无敌!李先txt百度云上品寒士陈操之娶了谁第二章悔婚退魔部特殊报告记录在哪看但平民万人迷by可以悔婚吗我在星际学考古铃兰在线阅读李先天下无敌!无防盗章节列表铃兰我在星际学考古免费全文笔趣阁李先天下无敌!全文大结局无弹窗李先天下无敌!完整版免费李先天下无敌!免费全文笔趣阁哈利波特之我是传奇无弹窗铃兰我在星际学考古最新更新章节免费阅读天下无敌!李先百科大全天下无敌!李先全文完整版铃兰我在星际学考古全文大结局无弹窗她没来迟鱼不忆99百度天下无敌!李先在线阅读铃兰我在星际学考古无弹窗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什么意思天下无敌!李先笔趣阁最新列表万古武帝秦风斩仙台上何人?灵台方寸关门弟子短剧铃兰我在星际学考古小说TXT无错版铃兰我在星际学考古笔趣阁无防盗开局揭皇榜,皇后竟是我亲娘官途,搭上女领导之后!千里宦途升迁之路官道征途:从跟老婆离婚开始权力巅峰:从城建办主任开始官梯险情相亲认错人,闪婚千亿女总裁二嫁好孕,残疾世子宠疯了不乖官路女人香学姐蓄意勾引深入浅出仙帝重生,我有一个紫云葫芦财阀小甜妻:老公,乖乖宠我空白在综艺直播里高潮不断重回2009,从不当舔狗开始透骨欢爱欲之潮NP万人迷她千娇百媚[穿书]大明:我只想做一个小县令啊官场:从读心术开始崛起逆袭人生,从绝境走向权力巅峰清穿后被康熙巧取豪夺了装疯卖傻三年,从边疆开始崛起官阶,从亲子鉴定平步青云!逆袭人生,从绝境走向权力巅峰小药店通古今,我暴富不难吧?前门村的留守妇女笔趣阁寒门官路2:权变前妻太撩人:傅总把持不住了官阶,从亲子鉴定平步青云!大秦第一熊孩子一问小说网秘书太厉害,倾城女领导直呼受不了驾崩百年,朕成了暴君的白月光我和我妈的那些事儿(无绿修改)合欢御女录荒岛狂龙直上青云深度补习>上流社会共享女友镇龙棺,阎王命上瘾禁忌爱欲之潮假千金身世曝光,玄学大佬杀疯了臣服议事桌上的官途:权力巅峰开局手搓歼10,被女儿开去航展曝光了!关于我哥和我男朋友互换身体这件事村野流香闪婚夜,残疾老公站起来了师娘,你真美迟音官妻太荒吞天诀乡村绝色村姑九天剑主春漾穿成虐文主角后我和霸总he了日复一日真千金霸气归来,五个哥哥磕头认错机娘世界,校花老师要上天了农门医女:我带着全家致富了大明:诏狱讲课,老朱偷听人麻了四合院:带着娄晓娥提前躺平蛟龙出渊,十个师姐又美又飒!被骂赔钱货,看我种田跑商成富婆悟性逆天:模型机悟出龙警3000!脱下她的情趣内衣山雨欲来离婚后,渣爹做梦都在偷妈咪小夫人奶又甜,大叔彻底失了控我委身病娇反派后,男主黑化了图谋不轨七零甜蜜蜜,糙汉宠翻小辣媳末世:开局疯狂囤物资,美女急哭了千亿总裁宠妻成狂病弱太子妃超凶的医妃她日日想休夫放开她,让我来财阀小娇妻:叔,你要宠坏我了!网站tag地图网站地图四合院从截胡秦淮茹开始! 分解吧 四合院从截胡秦淮茹开始免费阅读 四合院从截胡秦淮茹开始 始终不孤独 四合院从截胡秦淮茹开始张元林 四合院从截胡秦淮茹开始最新章节列表 四合院从截胡秦淮茹开始真的在写了 四合院从截胡秦淮茹开始最新章节 四合院从截胡秦淮茹开始 徐天策 四合院从截胡秦淮茹开始躺平 四合院从截胡秦淮茹开始林青山 四合院从截胡秦淮茹开始! 四合院从截胡秦淮茹开始 真的在写了 四合院从截胡秦淮茹开始TXT 四合院从截胡秦淮茹开始 四合院从截胡秦淮茹开始作者真的在写了 四合院从截胡秦淮茹开始! 鸡仔001 四合院从截胡秦淮茹开始!(鸡仔001)免费阅读 快穿:我成了反派崽崽们的白月光 我的兵王女友 NBA:从折磨乔丹开始加点升级 万能修改器 追你时你不在意,我订婚你哭什么 被休后,我盖房屯粮肉满仓 唠唠叨叨人生笔记本 疯批大佬缠着叫宝宝!一脚踢飞 秘书的沦陷之路 我的1999 大胆热恋:霍总怀里撒个娇 先抛夫,后弃子,离婚后她爽翻了 我在无聊的生活里混日子 我在诸天有角色 全宗门穿现代,满级大佬带飞祖国 一吻定情:大叔,把持不住 连通 是谁偷走了我的百亿集团 盖世神医 仙府长生:谁让他这么御兽的!
本月排行榜
- 性开放的世界橘子爱吃橙子
- 直男交易赛赶赶
- 惜春容秦柒
- 母爱芳土的沉沦フ?ルー
- 我网恋又翻车了头脑发热
- 女配只做路人甲(穿书NPH)耳东小姐
- 师娘赶下山:九个师姐绝色倾城芝士脆
- 新回首苍凉刺缘
- 干涸地火风L
- 难逃阿里里呀
- 家庭调解员ximan
- 被健身房教练秘密调教后百无禁忌
- 爱你是我们的本性我喜欢吃肉
- 狂医下山,都市我为王醉西风
- 对面邻居不拉窗帘小花灯糕
本周收藏榜
- 癌症晚期,高冷老婆疯狂报复我清酒一壶
- 幼儿园里的黑人小鬼同学,把可爱的黑丝吊带肥臀妈妈爆插到恶堕叫爹!琴师
- 爱你老妈煽情
- 被我催眠的一家人(无绿修改版)快乐的老色批
- 人妻调教系统淫妇章鉴
- 可怜的社畜东度日
- 被欲望吞噬的凌嘉竟将美琪美雪两姐妹抓住当做自己泄欲的工具大可爱萝莉资本家
- 表弟的百宝箱之妈妈淫戏孤独的大硬
- 冷艳美母是我的丝袜性奴佚名
- 巨乳萝莉留下来hulu
- 昏迷后的教师妈妈被一群小鬼瞒着儿子肏成人肉飞机杯,穴里塞满垃圾高潮喷水!hulu
- 将美母人妻驯服为胯下渴求大鸡巴的性感雌鹿坐骑cbh
- 美艳性感的陪读妈妈撅起白嫩的美臀爱肏熟女的小正太
- 龙族堕落调教sxsy.org
- 幼儿园里的黑人小鬼同学,把可爱的黑丝吊带肥臀妈妈爆插到恶堕叫爹!(无绿改)珍稀木种塞林木
最新更新
- 重生1958:发家致富从南锣鼓巷开始小鱼吃辣椒
- 致命打击:枪火游侠佣兵路耗子爱吃鸡腿
- 重生之浪王之王吹个大气球9
- 重生鉴宝:我真没想当专家眀智
- 华娱从代拍开始华尔街扛吧子
- 说好艺考当明星,你搞神话战魂?傲无常
- 游戏制作:从重铸二次元游戏开始月莹夜
- 师命难违,绝色总裁老婆我来了狼行北上
- 从下乡支医开始重走人生路我是小木子
- 最强狂兵Ⅱ:黑暗荣耀烈焰滔滔
- 满级大佬:我竟然回了新手村绝境中的人
- 得罪资本后,我的歌越唱越红不是蒜是水仙
- 人生消消乐后,我财富自由了绿豆真好吃
- 娇惯(校园1v1)一个珍惜xp的小女孩
- 迷乱光阴录kill4300
新书入库
- 杏雨重明月明中
- 守住秘密真的很难(陪妈妈换妻)佚名
- 吴哥窟克服拖延症
- 霓虹夜与白鸽子(金主)婉墅
- 网黄女主播含精量
- 刑之迷恋神之救赎
- 用华夏大肉棒将相亲相爱的东洋和西洋美少女彻底征服卍科甲
- 软狗不是兔子
- 错位囚笼木三观
- 奸爱小白蛇